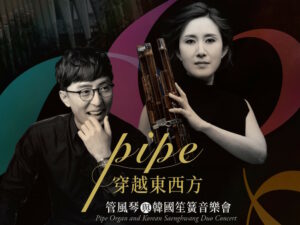青年管風琴演奏家林婉瑩,畢業於德國斯圖加特國立音樂和表演藝術大學管風琴演奏及教會音樂雙主修,師從學界泰斗Dr. Ludger Lohmann教授。跟著先生四年,想起先生踏踏實實的教學,事皆要切,再度與讀者們分享她得自盧曼教授的管風琴專業訓練。
婉瑩2020年6月畢業後,旋及獲得法國圖盧茲 Toulouse 交換學生獎學金,於2020年8月赴笈法國跟隨巴黎高等音樂學院管風琴教授、與巴黎聖母院管風琴師 Michael Bouvard 學習!
我本是一個不善執筆的人。跟隨先生學習四載,非無事可敘,只是所學所獲,皆源于先生的一言一行,非寥寥幾筆可以概括。先生授我一技之長,更教我做人的道理。才疏學淺,借此文回憶四年點滴,記錄從先生那得到的所學所感,也希望讀者能有所啟發。
#練習的真諦
練習的真諦是什麼?對於這個老生常談的話題,每個人都看似心知肚明。練習的真諦——簡單但並不容易——慢。然而,慢,不僅在於練琴速度,更要慢於心態。剛入先生門下的我,常常自責自己學得太慢,總是急於求成。而每當我懊惱時,先生總會安慰我:「慢慢來,不要急。」先生口中的慢,雨露般澆灌著我,慢慢陪伴了我四年的成長。
當然,除了心態,練琴技巧也十分重要。如先生所言,先完整演奏一遍,找出困難的片段,再將練習片段精確到某一小節甚至某幾串音符,直擊要害。然後用匠人精神去不斷打磨,加以反覆練習,是笨辦法,卻也是捷徑。掌握了困難部分後,再將練習範圍擴大到樂句,最後到樂段,每天循環往復,除此之外,別無他途。
比技巧更重要的,是「溯源」。演奏早期古音樂時,先生會帶著我嘗試早期古式演奏指法的使用,任我在繁複而又華麗的裝飾音世界裡盡情探索;演奏巴赫的聖詠前奏曲時,先生會同我分析旋律線條與歌詞、和聲之間的關係以及背後的象徵意義;演奏馬克思・雷格 Reger時,先生不僅會滔滔不絕的談起作品的時代背景和作曲家生平,更會放大鏡般分析樂曲中的每一處動機並尋找彼此的關聯。只有全方面剖析作品,才能增加在音樂理解上的寬度和厚度。
不僅如此,作為古典管風琴音樂的擁護者,先生仍然保持開放的心態,鼓勵我們大膽嘗試。最愛「離經叛道」的我,總不滿足於演奏古典音樂。我嘗試過管風琴與各種元素的多元結合,從當代音樂、到電子音樂,再到中國元素……每次玩得不亦樂乎。當我興致勃勃的將作品展示給先生看時,總能收到先生的鼓勵和表揚。來到法國學習後,我與圖盧茲的搖滾組合Bruit合作了一支管風琴與搖滾音樂的作品。聽了一輩子古典音樂,已是花甲之年的先生,看完這支長達10分鐘的搖滾音樂視頻後,一邊誇一邊問:「老實說,這個架子鼓就不能消停幾分鐘嗎?」
#壓力的另一面
在德語中,有個形容上臺緊張的詞,叫Lampenfieber。 Lampe, 是燈的意思;Fieber, 意為發燒。Lampenfieber, 翻譯過來,就是聚光燈下的恐懼。每一位音樂家,多多少少都患有Lampenfieber.。在台下積攢了十二分的努力,由於緊張,在舞臺上常常只能發揮八成,令人沮喪。與先生聊起,先生坦言,就算是舉辦了無數場音樂會的他,也難免會感到緊張。對此,只有靠日復一日的演奏來積攢經驗,從而緩解壓力。老一輩演奏家,身經百戰,對於已演奏了上百遍的曲目更是了然於心,在臺上自然會比年輕的演奏家們自如許多。然而,身處壓力和緊張的同時,身體分泌的多巴胺,能夠調動音樂家的情緒,使音樂更加生動而有朝氣。而這一點,對於演奏家來說,也是彌足珍貴的。誠如維特根斯坦所言,「問題的解決源於問題的消除」。也許,緊張感並不是需要解決的問題,而是一種與之共處的狀態。
當我們看到壓力的另一面後,你是否能夠不再排斥它呢?
#指尖之上心靈之間
當你經過斯圖加特音樂學院的琴房,有時,你會看到先生與學生坐在琴房外的長廊上,喝著咖啡聊著天。先生不僅彈得一手好琴,更練就了識人知心的本領。
初到斯圖不久,對一切「水土不服」,磕磕撞撞中的我難免心緒繁雜。某日在課上,我彈奏了一首巴赫的聖詠前奏曲。一曲終了,一陣短暫的沉默後,先生問我是否一切安好。我詫異,先生接著說:「你雖然什麼都沒有提起,但是我能聽得到。聽音樂,要用心。」
先生也有孩童般可愛的一面。偶爾,他會學著年輕人,用短信給我們發送可愛的表情包。在學生生日時,他也會興致昂揚的坐在琴上,一邊彈奏,一邊和學生們一起合唱生日歌慶生。來自五湖四海的學生,大家性格各異,演奏風格更是千人千面。而先生總能以海納百川般之態,在為我們烙印上德派音樂的同時,包容並鼓勵我們塑造自己的個人風格。就這樣,先生不僅授課,並且授心。先生用他的人生智慧與款款溫情,治癒了一代又一代的學子。
先生不僅待學生用心,也常教導我們,在音樂上要保持一顆「#童心」,不要忘記音樂的初衷。在我遭受挫折,將要放棄之時,是先生的音樂,如清泉流入心田,也如牧羊人輕撫著羊羔一般,撫慰著我,鼓勵著我,告訴我,在風雲歲月中,永遠在心裡,為音樂保留一方乾淨純粹的土地。
我想,這就是先生的黑白之道。
文/林婉瑩
曾受邀在多個知名國際音樂節上擔任演奏嘉賓,包括法國圖盧茲管風琴藝術節、法國Pablo Casals音樂節、德國Stiftsmusik 音樂節等。2017年,她所創作的第一首管風琴和電子音樂作品《Monolog》,在義大利Savorgnano進行首演。2020年,她與來自法國圖盧茲的搖滾樂隊 “Bruit” 合作錄製了他們的第一張專輯。她的演奏足跡遍佈中國、德國、法國、西班牙等地,廣受好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