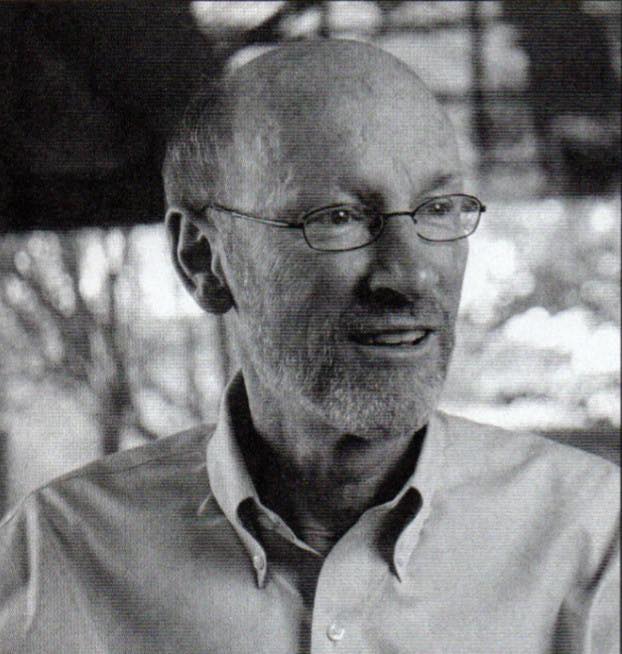

本刊委請Dr. Alain Truche (DMA, student of Dr. George Ritchie at UNL.) 聯繫本文作者 Dr. Paul Barte與TAO雜誌授權翻譯轉載,在此一併致謝。
『You have the Guild’s permission to post the article on the Orgelkids Taiwan Facebook page. Copyright 2020, by the American Guild of Organists.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Organist magazine.』
Barte:你曾在巴哈研究班上受教於Christoph Wolff,可以談談那次的經驗嗎?你從他學到了甚麼?對你的演奏有什麼影響,還是使你更能從知識、歷史或分析的角度來處理音樂?
Ritchie:我剛接觸Harald Vogel不久,就有幸於1977年夏天參加Christoph Wolff在哈佛大學開辦的國家人文基金會巴哈研究班,這個經驗也對我的專業生涯和教職與演奏的發展有重大影響。我們那時候研讀了Philipp Spitta在19世紀撰寫的巴哈傳記這部重量級巨著,還有Wolff剛完成而即將發表在《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上的巴哈研究專文,作為我們的基礎,這些內容成為研究關於巴哈的第一手資料(當時有許多資料剛被發現不久)的出發點,也可以用來從你所提到的各個不同角度探討巴哈生平和音樂,包括知識、歷史和分析方面。這對我的其中一個影響就是,讓我知道像Wolff這樣的重要學者,是如何緊密根據歷史材料,發展出針對巴哈生平和音樂的想像性見解。Wolff的研究班和Vogel的影響,都促使我盡可能把演奏者和教師的身分奠基在17世紀和18世紀的巴哈音樂手稿(能夠拿到的話),還有巴哈的學生和同時期人士抄寫的複本。我在準備錄製巴哈全套管風琴作品和《賦格的藝術》時,這個方法格外重要。那次研討會之後,我就很積極參與美國巴哈學會(American Bach Society),而我第一次參加ABS雙年會時,就聽到Christoph Wolff和George Stauffer發表研究巴哈管風琴音樂的報告論文。於是我們便邀請他們在內布拉斯加大學林肯分校於1980年舉開的管風琴研討會中擔任主要講員,那次的主題就是「巴哈與管風琴」,後來我就與George Stauffer合著了《管風琴技巧:現代與早期》這本書。
Barte:據我所知,André Isoir (附圖)也對你有很深的影響。你去跟他學習的緣由是什麼?是什麼時候的事?
Ritchie:我在德國向Helmut Walcha學習德國音樂的那段時間,得到非常多收穫,所以我也想去法國拜師學藝。1976年AGO在波士頓舉開全國大會,Isoir開課進行一個星期的大師班,我全程參加而且對他非常欽佩,也很仰慕他的錄音。所以在1982年休假進修年間,我就到巴黎向他習藝3個月,那段經驗非常美妙:我通常會先聽過他彈某一首樂曲的錄音,然後盡可能按照他的方式彈給他聽,然後他再用第二種、第三種方式彈給我聽。換句話說,他會示範好幾種可能性,不是只有單一的「正確」方法來彈這個作品。如果在我比較年輕的時候這樣作,我可能會被搞亂,但是對當時的我而言,這種教學方法很愉快又很刺激。他的法國經典曲目紮實地以第一手資料為依據,但他使用自由又即興的方式彈奏,這對我很有幫助。此外,到法國學藝讓我得到期待已久的收穫,在此之前我演奏過法國音樂也在課堂上教過,但一直是偏愛德國音樂,總覺得法國音樂雖然風格優美,內涵卻不像德國曲目那麼深刻。那時我開始了解,法國人把風格視為內涵實體。例如,重點不單在於食物吃進口時的味道,也在於如何擺盤;不只是你所講的詞句,也在於你講話的神情態度。我開始看到,法國的序曲風格對於全歐洲各大作曲家都有重大影響;用17到19世紀的古老法國管風琴彈奏這些曲目時,這些音樂會以我意想不到的方式復活,讓我體會到音樂中原本令我困惑不解的部分。
Barte:你剛才提到在加州雷德蘭茲大學就讀的事,之後你還到美國的哪些地方進修?
Ritchie:我在雷德蘭茲大學就讀期間向Leslie Spelman學習管風琴,1962年取得藝術學士學位,然後進入Raymond Boese門下攻讀碩士,1963年得到音樂碩士學位。Boese本身就是Helmut Walcha的學生,所以我也想拜Walcha為師。我到法蘭克福向Walcha學習之後,就到紐約的協和神學院攻讀聖樂碩士,向聖樂學院的院長Robert Baker學習管風琴,此外也向聖公會耶穌升天教會的管風琴師兼詩班長Vernon de Tar習藝,到1967年取得學位。這些老師都是非常出色的教練,但是對於基本技巧著墨不多。我在紐約聽過Clyde Holloway演奏,非常欽佩他的高超技藝和流暢靈活,所以就到印地安那大學拜他為師,後來就在1975年獲得音樂博士學位。到了這個發展階段卻專攻基本技巧,感覺不太尋常,但是因為在Holloway門下大量的技巧練習,尤其是鑽研Harold Gleason的《管風琴彈奏法》,讓我在演奏時更具有技巧上的穩定性,對於後來和George Stauffer合著的《管風琴技巧:現代與早期》帶來莫大的幫助。
Barte:我知道你還曾在杜克大學待過一段時間,你是在印地安那大學拿到博士就去杜克嗎?那時候負責什麼工作?
Ritchie:我在1969年的秋天到杜克擔任教堂管風琴師和音樂部助理主任,那時候我剛結束博士班全時生的階段(我後來在1975年取得博士學位)。我在杜克待了3年,在莊嚴的新哥德式大教堂裡服事,為240人的大詩班伴奏,也擔任大一女聲合唱團的指揮,並且在音樂系教管風琴課。滿3年之後,內布拉斯加大學林肯分校要聘我為音樂系助理教授,薪資比杜克優沃很多;杜克也調高薪資,願意給我助理教授職位而且以後有機會成為終身職,還讓我繼續擔任教堂管風琴師。杜克開出的條件很有吸引力,但是我在杜克雖然有很多很優秀又有天賦的管風琴學生,但都是在大學部,而且多半不是音樂系的。而在內布拉斯加大學林肯分校,我除了教大學部,還有機會教碩士班和博士班研究生,其中有很多人會想以專職管風琴師為志業;此外我可以為大學部和研究生開設各種課程,包括管風琴作品、音樂史、巴洛克演奏練習等。在杜克大學工作期間,我也明白自己最大的滿足來自教學和管風琴獨奏音樂會。我身為管風琴家,比較想要專注投入學習和精煉某些管風琴獨奏曲,而不是經常變換曲目的合唱伴奏或聚會時的管風琴演奏,所以我作出決定,在1972年秋天搬到內布拉斯加。當時有些人很納悶我為何選擇離開東岸,而我當時和現在的回答都是:我覺得全國各地都很好。不出所料,中西部大草原的自然環境、歷史和文化真的非常迷人,大學本身和同事們創造出很能激勵知性的環境,之後的34年當中,我就在那裡開展自己的專業生涯,而內人Joy也在英文系有很好的發展。我們的兒子Aaron在1975年出生,Lincoln市也是個非常棒的成長環境。(待續)
本文出自”Interview with George Ritchie in January 2020 issues of TAO”
中譯: 劉思潔 (專業翻譯,Orgelkids Taiwan文字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