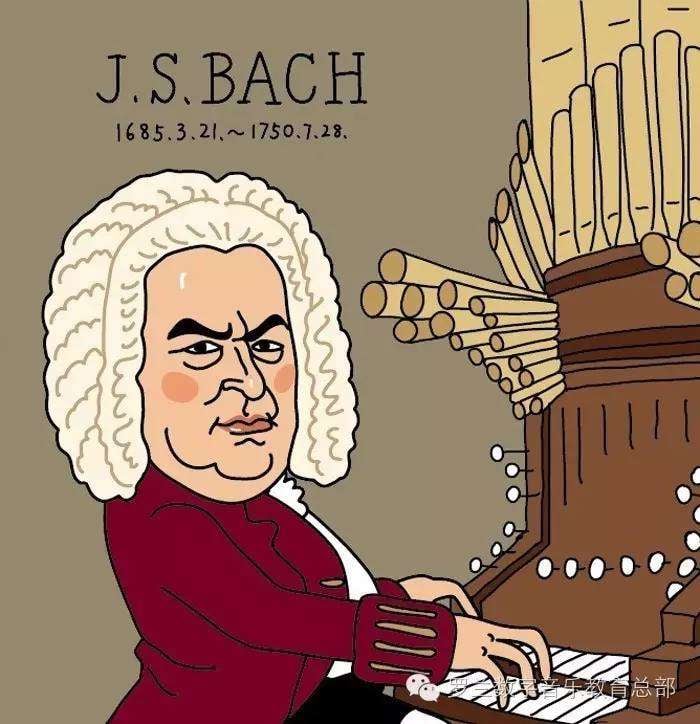我有個聽巴赫的朋友,沒什麼深交,更多的是神交。他不彈鋼琴,CD也不多,常常是開車過山的時候聽巴赫的鋼琴音樂。他就是給我租的公寓修理設施的工人羅伯特。
一副“老大哥”的健壯身型,腦後一條粗辮子的愛爾蘭後裔羅伯特經常開車旅行,一定得聽電臺裡的古典音樂。他粗聲大嗓地說:“我每次開車過山時都聽巴赫!”
老天,那是什麼感覺?我在城裡普普通通的街道中開車有時也聽音樂。用“道路”去感覺音樂,簡直就是把音樂“種”在自己的記憶和生活裡哪。音樂鋪路,那路就是發著柔輝的愛之路,而有了路,樂境好像突然寬闊深遠起來,沿途吸收著人間煙火的溫暖。而在山裡開,還有白雲,還有積雪呢……
羅伯特拿過地質學位,也曾是辦公室裡的白領,後來嫌不夠自由,乾脆當了上班時間不固定的工人。他常在遙遠寒冷的阿拉斯加住,跟當地人一道獵鹿。“最冷的時候就在家安安靜靜地讀書。我收藏了好多書!”這樣的怪人我當然喜歡了,每次家裡的壁爐壞了都高高興興等羅伯特來,連幹活帶跟我神侃。我沒跟他討論過版本,甚至沒問過他喜不喜歡我心愛的古爾德。我更樂意聽他說在那個比加拿大更靠北的地方的故事。那裡的湖水冬天在冰雪簇擁下是銀灰色的,還有桔紅嘴巴白肚皮的海鸚,還有身材如羅伯特般彪悍的捕魚人。我知道他在那個冷得清澈的地方不光獵鹿,還把巴赫的《英國組曲》,《賦格的藝術》等等都聽過了。一般聽這些音樂的人總有些“理由”,也許羅伯特只是想放鬆一下,也許只是覺得巴赫的聲音最合口味。我不忍問,把自己對古爾德的嚮往也悄悄藏著。
今天我就要從這所房子搬走,也就是說,再也見不到羅伯特了。收拾東西的時候又聽巴赫的Partita組曲,忽然後悔,幹嗎沒跟羅伯特談談古爾德呢。你一定喜歡他的,羅伯特。
你聽,當《賦格的藝術》在古爾德指下響起時,那鑲著銀邊的管風琴聲像溪水一樣在五線譜裡蜿蜒,我好像在這座深山裡跟著它,伴隨蒼崖雲樹走啊走。巴赫把主題顛過來掉過去,像擲骰子似的寂寞地玩著德國人的遊戲。古爾德更是自顧自埋頭輕唱著。我退到很遠很遠的地方,驚歎得捂住嘴巴不能出聲。最喜歡的還是他80年代彈的「哥德堡變奏曲」,從稀疏的星光般的主題開始,由珠玉之聲到雷電霹雹,那寒光閃閃的聲音裡深埋著寬展的柔情,悄然融化掉我們對這個世界所有的恐懼和緊張。好多好多次,我看著譜子,注視著旋律在左右手間怎樣穿梭,迅速砌起一座精巧剔透的建築,瞬間融化在風裡,然後出現新的一座。變幻的節奏,繁華的雕飾和鬼斧神工般的對位令聽者都一籌莫展。巴赫的音樂對演奏者和聽眾來說都是讓人“絕望”的世界。決定自囚其中的人,內心必有塊神秘而生生不息的樂土,不然如何在這森林般的蓊郁幽深之中開懷,找到被表面的平板枯燥深藏的生命之歌?讀了好多古爾德寫的東西或是採訪錄,最令我震撼的卻是那些他離開音樂的瞬間。
“我總是想起那些長長的夏夜。雪化了,野鵝和野鴨成群往北方飛。太陽升起的時候,空中還有最後一絲微光在閃。我喜歡坐在湖邊,看那些鵝和鴨子安安靜靜地繞著湖飛,我覺得自己仿佛是那平和的四周的一部分,我希望這樣的時光永遠不要結束……”
《旅居加拿大的管風琴家、作家、樂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