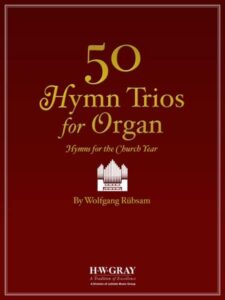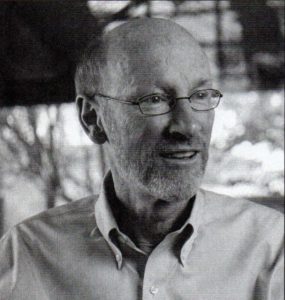學習西方音樂的人沒有不喜歡教堂的,在音樂家眼裡,那簡直不是一座建築而是一座音樂孵化器。音樂家認定自己是知曉宗教對音樂所起作用有著非同尋常理解的群體,因而愛屋及烏。不知道是不是其他行當也如此迷戀,但音樂家個個喜歡往教堂裡鑽,個個渴望踏進作曲家被攪動肝腸從而流出撼人心魄旋律的現場。歐洲音樂最打動人心也最超凡入聖的一類就是宗教音樂,它們大都出自像蒼穹一樣宏大也像蒼穹一樣無私施與作曲家以靈感的特定空間。斑駁窗畫的深處,蘊育出一組組勾心攝魄的樂句,讓遙聞《格里果聖歌》《彌賽亞》《莊嚴彌撒》《安魂曲》《聖母頌》的音樂家神魂顛倒。除了愛情,人類深宏精神的另一處湧泉就是宗教。音樂家要找尋母語,就得進教堂。因此,教堂與音樂毗連,構成音樂家回歸母體的方式。
霞光擁蔽·天光覆蓋
教堂擁有世界上體積最大、音響最強的樂器——管風琴。每座大教堂都被不同型號的音管覆蓋一面牆體,有的甚至於在不同牆面安裝了兩三組不同型號的管風琴。高高低低、粗粗細細、密密麻麻的管子,如同排炮,射出陣陣聲浪。未在教堂聆聽過管風琴的人,絕對想不到世界上還有如此龐大的樂器可以像牆體轟然倒塌一樣傾瀉出如此竦耳驚心的音響。仰若天庭的拱頂與繞梁而旋的天音,渾然一體,交於穹頂。聽得廢寢忘食走火入魔的音樂家,都能感到被震盪的驚悸和被輻射的陶醉。
建築雄偉,音樂柔曼,教堂包容兩極。對上蒼,教堂用唱詩班說話;對蒼生,教堂用管風琴說話。唱詩班把平民祈禱,上達天廳;管風琴把上蒼撫慰,普降蒼生。教堂是空間,音樂是時間。“宇”“宙”結盟,建築、音樂、宗教、科技,四者協同。於是,牆體樂器連體,建築音樂結盟,科技藝術聯手,聽覺視覺相擁。把音響放大到一堵牆,把一堵牆化為一片響。音響因教堂而神聖,教堂因音響變天堂。天音因管風琴普灑大地,大地因管風琴拔地升騰。“龐然大物”把所有樂器加起來都難以與其抗衡的音響,變為直抵上蒼的祈禱。噴出一股氣,轟倒所有人。聖詠從天而落,世界開始朦朧。
解構世界的科學不能讓靈魂感到幸福,應用科技的聲學卻能讓靈魂感到升騰。稀釋音響的巨大空間對音樂效果來講不一定好,對心靈迷醉來講卻事半功倍。拱形蒼穹使音響迷離,使精神恍惚,使靈魂朦朧,使淚眼婆娑。科學與幸福無關,科技卻與音響毗連。二者攜手,讓音響化為陶醉。如果把冷冰冰的音管比喻成懷著善意的科技吹向信仰的通風口,溫情的管壁就吐出了足夠嘹亮和透明的音響,讓每根管道,聯接浩天。科技不再冰冷,音樂不再獨行,宗教不再隔世,三股力量結為神聖同盟。
記得第一次在巴黎聖母院聽管風琴,頓覺霞光擁蔽,有種被深度擊中的搖撼。久耽音樂卻從未在此空間聽過音樂的人,已然不在凡界。那簡直不是音樂,而是一道天光覆蓋!像被扯住褲角,腿腳再也挪不動了。什麼是如雷貫耳?這就是如雷貫耳!什麼是餘音繞梁?這就是餘音繞梁!什麼是天籟天音?這就是天籟天音!什麼是聲振林木、響遏行雲?這就是聲振林木、響遏行雲!於是,幻境產生,刹那恒定。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境,沒有人理解音樂家未能及時走進教堂對於其所從事職業的缺憾的糾結程度,如同沒有看到過聖母像卻演奏《聖母頌》的人感到以前的“行徑”總有點不著邊際的輕飄。有機緣時常要走進教堂,力圖補上音樂家的缺課。我們自然不是把其作為遊覽地而是視其為體驗“儀式音樂”的視窗。
第一次參加基督教洗禮是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小教堂。洗禮結束,大家尾隨牧師走進教堂。甫一落座,音樂緩起。唱詩班的聖詠長達十幾分鐘,全場寂然,但聞天音。戶內戶外的對比,讓第一次接受洗禮也第一次觀看洗禮的人,深迷意境。童聲合唱,純淨綿長,猶如溪水。英文、義大利文或拉丁文的歌詞對我們來說全無意義,那只不過是用以表達虔誠甚至是鄉愁的朦朧音節。但音響繞梁,如直抵命脈的神針,劃開了每一個在場者的心扉。
錄放設備使人們誤以為坐在家裡聽巴赫與到教堂聽巴赫是一回事,閱讀儀式與參與儀式是一回事,其實,感受必須來自“整個系統”。兩種體驗之別猶如翻看印刷畫冊之於仰視西斯廷教堂真跡一樣。只有在教堂,音樂家才能聽到與建築合二為一的“壁壘”轟鳴,這是在錄放設備放不出來的“整體”。此時此刻,一個人聽到的不是一件樂器,而是一面“牆”!儀式音樂的感受不能從唱盤上獲得,必須站在“文化現場”——那是連閣雲漫的聲浪中令每個毛孔噴張、充分吸納“整體”的沉醉。
是教堂托舉音樂還是音樂托舉教堂
不知道什麼年代,教堂插入上蒼的高度到達了幾乎夠得著上帝的程度。“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李白從詩歌的“高度”,驚豔地劃開蒼穹;教堂從建築的“高度”,挺拔地劃開蒼穹;音樂則從靈魂的“高度”,大聲地劃開蒼穹。各門藝術,都從無法指認的高度,劃開精神蒼穹。
寫下這些自然不是要把進教堂拔高到對生命旅程做一番“形而上”思考的虛境,而是無緣踏進教堂的音樂家難免不把後來看到的景觀連接到初次演奏宗教曲目的記憶中,用以解釋其之所以產生了強烈吸附力的原因。生不逢時,在近乎心靈麻木的年齡才補上這一課,遲遲領略到降低了飛翔高度與晚來迷客親近的聖詠。一代人揮之不去的心結和翹盼終於得以補償。所以,路過教堂,總不免長久凝視,禁不住遙聞曾被長久阻隔的“天使和聲”。這大概是音樂人之所以喜歡教堂的原委。
傅聰說:“巴赫就是一座教堂!”還有人說:“管風琴就是一座教堂”,諸如此類的言說都是金句。巴赫鋪灑《莊嚴彌撒》普度眾生,韓德爾詠唱《哈利路亞》讚美上蒼,莫札特低吟《安魂曲》慰藉苦難。一部部經典都是“高徹雲表,非複人世之音。”它們猶如人類精神史的座座奇峰,讓人覺得教堂的確不是一座建築,而是托心入雲、天光雲影的“歌管樓臺”!如此說來,是教堂托舉音樂還是音樂托舉教堂,還真的有點說不大清呢。
文:張振濤 (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研究員)